今天,历史建筑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材料、形态、构件,以及人与建筑的关系等,都承载了重要的历史记忆。
很多去过日本的读者,都曾惊叹于当地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使用,比如奈良和京都的历史景观。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长、建筑科教授光井涉在其书作《历史建筑的重生:日本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用》(以下简称《历史建筑的重生》)中,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建筑的保护历程,以及这其中相关保护制度的建立和所面对的争议。从中读者可以看到,关于历史建筑的保护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而到底该如何保护历史建筑也一直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  奈良街头 奈良街头
建筑的历史价值得到肯定
据《历史建筑的重生》,直到16世纪中叶之前,历史建筑的存在价值都没有得到日本社会的承认。在彼时人们眼里,历史建筑中的“历史”意味着一种时间久长的陈旧,有损坏就修复,修复结束后照常使用。
而当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建筑以大量且快速的趋势消失时,其价值也开始凸显。“大约在战国时代向江户时代过渡的时期,日本出现了肯定建筑之古,有意维持其古老外貌的思想。这一时期,从古时延续至中世的价值观与社会结构崩溃,大量贴合社会新秩序的建筑物爆发式出现。在这种经历破坏之后的大建设时代,这种推崇历史建筑的思想似乎与整个社会的趋势相悖。”《历史建筑的重生》中写道。
所谓失去才想到珍惜。恰恰就是在这时候,建筑的历史价值得到肯定,甚至相关的保护制度也得以出台。比如16世纪兴建的那些城堡,在17世纪的一部法令中被禁止拆除,即便是修补也要维持原本样貌不变。“也就是说,这一严苛得不允许丝毫改变的城堡维护标准是由德川幕府强制推行的。在漫长的岁月洗礼中,那些得以保留下来的城堡由大名、藩及城下町的象征,转变为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视觉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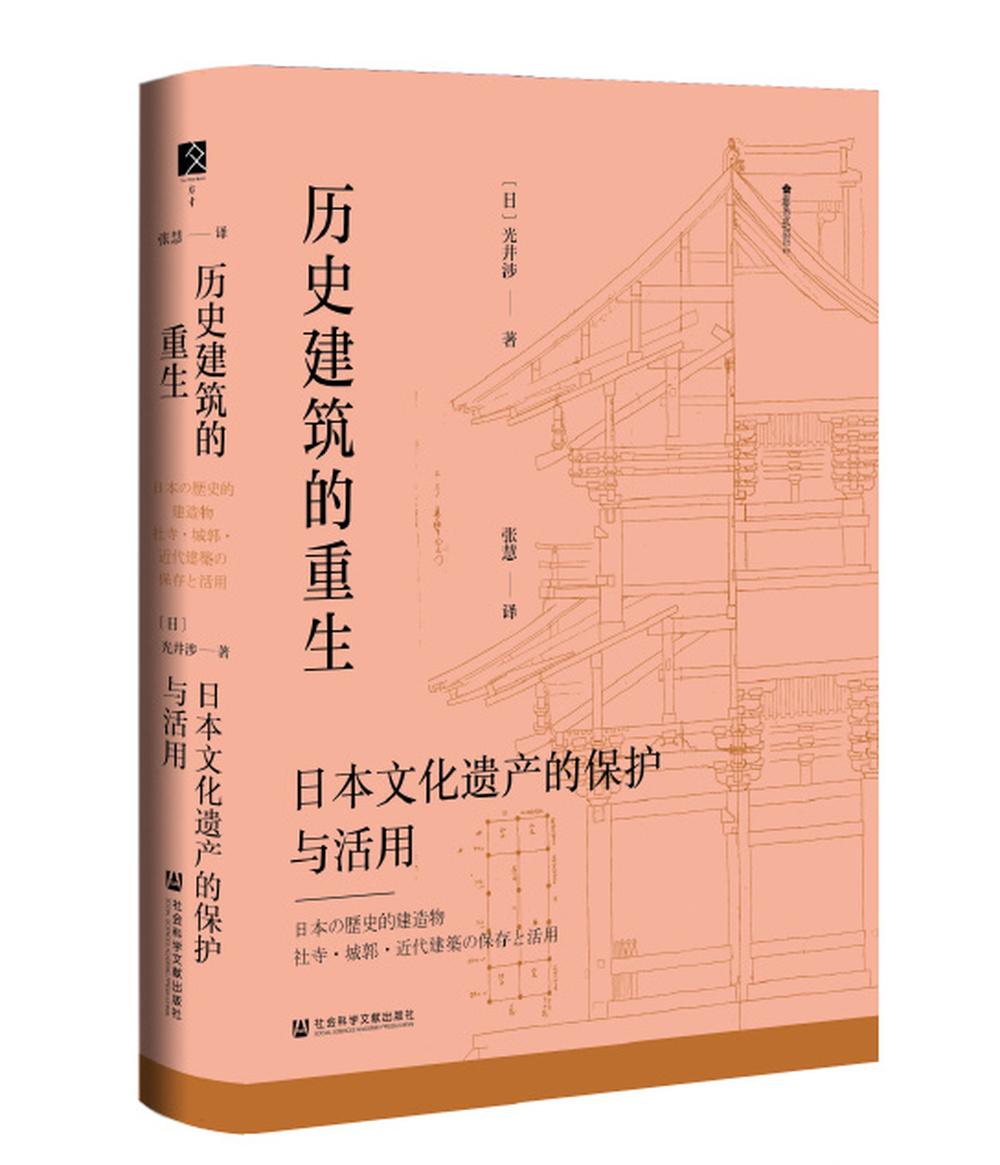
《历史建筑的重生》认为,如果说对城堡的保护受到了政治与制度的影响,那么对茶室的保护则关联着深层次的审美意识。
“茶室原本只是基于茶人个人审美和创见而设计建造的,但随着茶道流派和家元制(以家族血缘传承为主的技艺传承制度,多出现在日本传统手工艺与艺术的传承中),茶室的形式也一起固定了下来,成了衣钵相传的一部分。”
从意识到建筑的历史价值到为之指定种种评价标准,人们对历史建筑的认识过程是漫长的。据《历史建筑的重生》,直到日本江户时代中期,评价历史建筑的价值观才逐步确立,“在这一时期,人们明确意识到建筑的形态会随时代而变化,出现了尝试弄清楚相关变化路径的思辨性考察方法。”
而进行这一工作的重要人群来自于匠人世家。他们有着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了解建筑本身,也熟悉建筑的流派,他们研究建筑形态的变化,探究它们的起源,追寻那些消失的建筑。
《历史建筑的重生》认为,以上是发现历史建筑价值和理解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被认为是对历史事物的关心和向过去的回归。……人们虽然对历史建筑的价值有所认知,但此时并没有明确的保护意识。真正开展保护工作要等到明治维新后社会剧烈变动,近代建筑学登场的时候了。”
 奈良街头 奈良街头
指定为特别保护建筑或国宝
在建筑界,英国人乔赛亚·康德或许无人不晓。但是在这个专业领域之外,大概鲜少有中国读者知道,他被称为日本近代建筑之父。
据《历史建筑的重生》介绍,康德毕业于南肯辛顿美术学校和伦敦大学,在英国成就斐然。19世纪末期,他毅然前往日本,担任当时开始办学不久的工部大学校造家专业教授,为日本造家专业奠定了教学基础,而且他还是象征文明开化的鹿鸣管等一系列代表日本国家形象的建筑的设计者。他将自己在英国学习的建筑课程内容带往日本,以“术、式”为核心培养建筑人才。
彼时日本建筑学流行“折衷主义”。“不仅是要将建筑视为具有特殊形态的部分之集合体,在其统一的方式与各部分的比例之中找到蕴含的近似之处并分类,更是要重视风格产生的时代原因和背景精神。集合这些历史风格,重构并设计出新建筑的思路被称为‘折衷主义’。19 世纪的建筑师在设计建筑时正是以这种思路为基础的。对于折衷主义的建筑师来说,过去的著名建筑是新建筑的模范和样本,所以毫无疑问要保护历史建筑。这便是建筑学如此青睐历史建筑的根源。”《历史建筑的重生》中写道。
可事实上,有些历史建筑特别是寺院得以被保护,却是另外的原因,比如为中国游客所熟悉的浅草寺。《历史建筑的重生》中进行了相关介绍:“东京都的浅草寺如今是云集海内外游客的著名寺院。在经历两次火灾之后,浅草寺于17世纪中叶明确划定了寺院的范围,差不多比现在大了五倍。但如此广阔的区域并非全都是寺院本身,而是有许多商铺和出租屋。19世纪初仅仅是居住于此的世俗人士就有5000多人,正是这些地租支撑起了浅草寺的财政收入。”
19世纪末,日本推出了《古社寺保存法》,正式开始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其中规定:“社寺的建筑及宝物,尤其是值得成为历史之标志或美术之典范的,应咨询古社寺保存会,由内务大臣指定为特别保护建筑或国宝。”
众所周知,日本的历史建筑以木构建筑为主,其中有些经过多次修复,因此来自不同时代的构件成为人们辨别维修年代的重要依据,而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建筑修复的一些观点。
“建筑的现状是以往数次修复结果的累加,初看甚至无法分辨各部分的修复年代,只有修复时把构件拆下来才能知道。因此建筑物的修复方案不仅要考虑如何处理各个时代的痕迹,还要思考修复到什么状态合适。在众多选择之中,将建筑完全还原到初始样貌的‘复原’颇为显眼。”
 奈良街头 奈良街头
将历史建筑视为现代资产
建筑修复中的复原问题,大概在世界各地都难免争议,日本也不例外。
《历史建筑的重生》介绍,在1857年法国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中,建筑师维欧勒-勒-杜克以恢复到14世纪为由,创造性地复原了已经不存在的尖塔,而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烧毁的尖塔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对于维欧勒-勒-杜克的复原,当时有许多批评的声音,“其中最极端的批评是认为他打着复原的名义,进行穿凿附会的创作,修复结果和建筑原貌几乎毫无联系。”
日本一些建筑师的复原理念也招致批评。他们试图将建筑的模样尽量沿着时间线往前还原,但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经过多次修复之后出现于他们眼前建筑的模样。关于复原的时间点,建筑师并没有与社会达成一致。
另外,关于历史建筑在修复过程中能否维持原有的“古意”也十分重要。“在岁月的打磨下,建筑构件的表面逐渐老化。时光造成的破坏带来历史沧桑感,也从视觉上将历史建筑和现代新建筑区分开来。”可是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重新粉刷墙壁、更换新的构件会使建筑物完全丧失古意。在后来的一些历史建筑修复过程中,建筑师意识到不仅建筑的结构,就连材料的质感都要完全复原,以体现原有的古意。可是,即便这样做也需要面对批评。虽然十分重视建筑本身能体现历史感的古意,但将新增的材料做旧,将现代修复的地方做成历史建筑的一部分,却被认为是在“捏造历史”。
“但如果新材料不做旧的话,恐怕就会修复成新旧部分彼此割裂的补丁式建筑了。……对于构件表面老化所带来的古意,并没有某一种理解可以成为正确答案,多种价值观念是共存的,从不同角度思考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历史建筑的重生》中写道。
保护历史建筑的职责当然不是只属于建筑师。据书中介绍,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各地开始了街区保护运动,重视良好的生活环境。同一时期,日本各地出现了景观建设的风潮,以将各地区特有的历史景观用在现代城市建设当中。而到了2020年末,越来越多的历史建筑被列入一系列项目的保护对象。《历史建筑的重生》在最后写道:“大量历史建筑长期存在着,只是一直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而被忽视。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关注它们,将它们视为现代资产,或者说视为那些展望未来的城市建设的核心。”
來源網址: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794211407050213598 |